文/柏邦妮

她坐在化妆镜前,穿着白色小礼服。用一条黑色大围巾,裹着,严严实实的防止。缠绕得恰到好处,让我误以为,那条围巾是礼服的一部分。头发怎么弄,她有自己的意见,不再是唯唯诺诺任人摆布的小女孩。她不喜欢梳得很死很僵的发型,希望自然一点,再自然一点。她知道自己要什么。
拍照的时候,她轻微转侧面庞,角度给得准确而微妙。在外人看来,也许毫无变化,但是在镜头里,那一细微的一毫米,就是“好看”到“完美”的距离。摄影师为她着迷,不断的呓语“漂亮漂亮漂亮”,就像男人情动时刻的催眠。她的状态是一个成人的状态,享受这份恭维,此时此刻愿意相信。这一种相信是一种配合,你知道,在她心里,与这份沉浸有一段距离。她知道自己该给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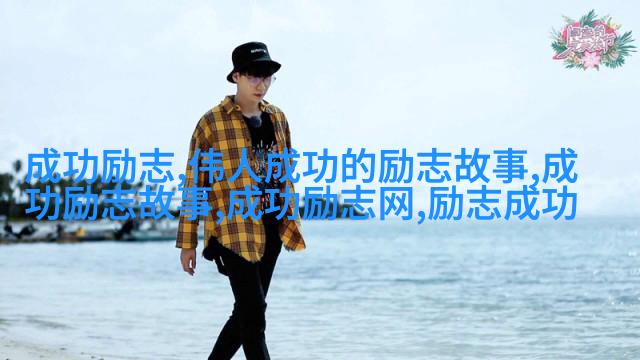
拍照结束,她穿回自己的衣服。一件大大的灰色毛衣,肘弯处起了毛球。头发全部梳起来,手背上有一块新伤,做家常菜时不小心烫的。蓝色牛仔裤,绑带旧皮靴。她弯下腰去,鞋带太长了,在脚腕处多绕了一圈,然后系上了。
当她弄完这些,又回到你认识她的那个女孩儿。你记得那个时候,她乖巧地坐在你面前,一双脏球鞋仿佛随时准备踏上新的征程,而全程都举着录音笔。那天夜晚,我们继续电话访问,因为信号不好,她维持着同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她知道自己原来是谁,现在是谁。

她曾经害怕创造,因为需要能力。而现在,我最害怕生活无聊、工作乏味。我希望一切都能多变化、多创造,每个角色都不一样,每段爱情都点亮我。我希望自己不是建立在对方悲喜上的,有自己独立的灵魂和生活。
演戏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在其中我成长为我自己。当陆川对我说:“你在演的是你想成为的人,但不是真正的人。”那是我自我成长过程中,最深刻的一个体验。他的话让我开始思考:真正的人,是什么样?

《南京南京》是我自我成长中的一个极致体验。在那部电影中,我遇到了一个极端状态——浓度很高、密度很高,却又笨拙坚持,就像一根绷到了最紧的地步。那时候,我已经被误解和侮辱压到了爆发点,我豁然开朗:“为什么要管?让他们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逆生长,这就是我的故事。我从二变成了二,更添了一分几分勇敢与坚持。这一次,从体育界走向娱乐圈,再次尝试跳出舒适区,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更高更远的事业目标。不论结果如何,只要能够不断挑战自我的边界,即使再次失败,也不会后悔因为它是我勇敢的一跃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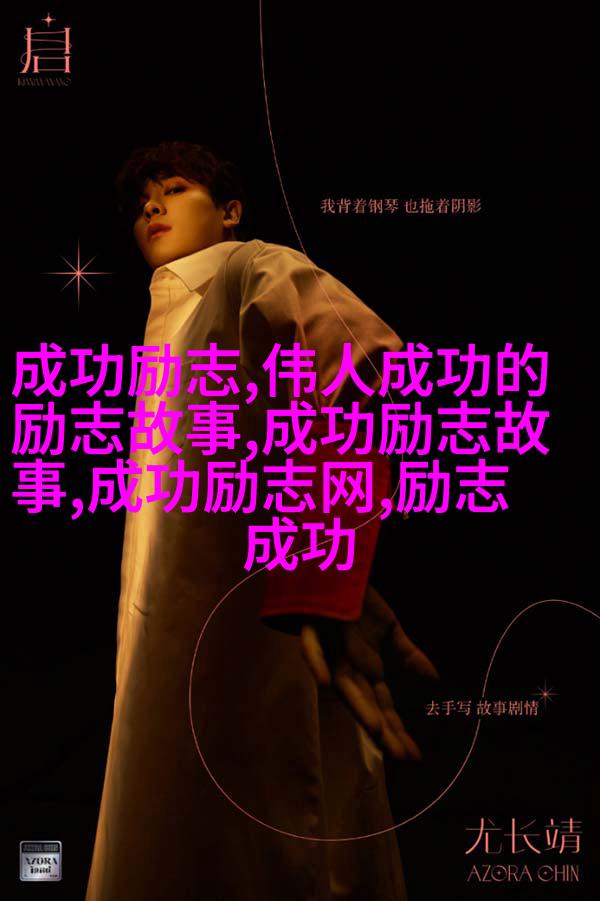
所以,当有人问起关于我的职业身份或生活态度时,我会笑而不语,因为只有那些真正了解过深层次的人才会明白,即便身为明星,我依然渴望更多地参与到那些让人心醉的事物中去,无论它们是什么形式,只要它们能激发出内心深处那股无法抑制的情感波涛即可。我想要超越既有的框架,用更加丰富和真挚的心灵语言与世界交流,所以尽管有些路途崎岖艰难,但每一步都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和空间而努力奋斗。而这一切,都源于最初那个对话:“我们可以一起越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