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吉姆结婚时,他还是大学生,常与朋友聚会。自我们长子出世后,吉姆与我很少外出。他的好友雷每周六下午来家下棋,我起初并不喜欢这个直率而固执的男人。他负责带啤酒,而我做三明治和薯片,他们的到来让我可以静悄悄地阅读一本书、享受牛奶带来的安逸。

对吉姆和雷来说,无论是晚餐、下棋还是激烈辩论,都能让他们心花怒放。我才明白,他们争论只是为了那份激辩的乐趣,每次他们都像故意挑选议题,再确定立场。我偶尔提醒他们小声点,不要打扰邻居,更不用说孩子了,但孩子总是在他们膝上睡着。我喜欢躲在旁边听他们争吵,他们是我所见过最聪明的男人。
啤酒箱渐渐空了,吉姆虽然瘦弱,却还想与兄弟比高低。雷喝酒从不上头,吉姆就输给他——有时候例外。当夜深人静,我盖上了毯子,就让两个人继续沉睡。

一次,医生诊断吉ム得了严重肾炎,一定四个月内不能饮酒,只能每天喝酸果汁,这对他来说几乎是苦刑。他不想让学校的人知道,所以打算取消与雷的约定。但我提醒他:“如果取消,那么所有计划都必须改变,不如就不要取消。”所以,我没告诉吉姆,就给雷打电话,让他知道一切。雷保证知道该怎么办。
星期六暴风雪持续了一整天,当晚饭准备好了,我们等待着雷是否会来。电话线中断了,也无法联系他。他准时来了,看起来像个雪人,将一箱啤酒放在二楼门前。不用开口,我的焦虑已被捕捉到。在帮忙拿外套时,他冲我轻轻摇头。我即将说话,被吉姆瞪了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警告:“别说出你那个该死的事实。”

接着,他从啤酒箱里抽出瓶装酸果汁,“咕咚”喝了一大口。而另一瓶装的是酸果汁!然后,雷开始谈论“真正的友谊”,斥责 吉姆不信任他,不诚实,还不听医生的话,对着啤酒瓶狂饮。这次发作惊醒了宝宝,他抱起孩子,在怀里祈祷这位小家伙长大后不要像父亲那样固执。
之后几个月里,每次预备好的都是酸果汁,而不是啤酒;但是由于憎恶酸果汁,最终改为咖啡和苏打水。我加入到了他们中间,最终学会了下棋,但技艺仍旧无法敌得过他们。终于能够参与讨论,被夸奖拥有良好的口才,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无所不能讨论,从远行理想开始探索未知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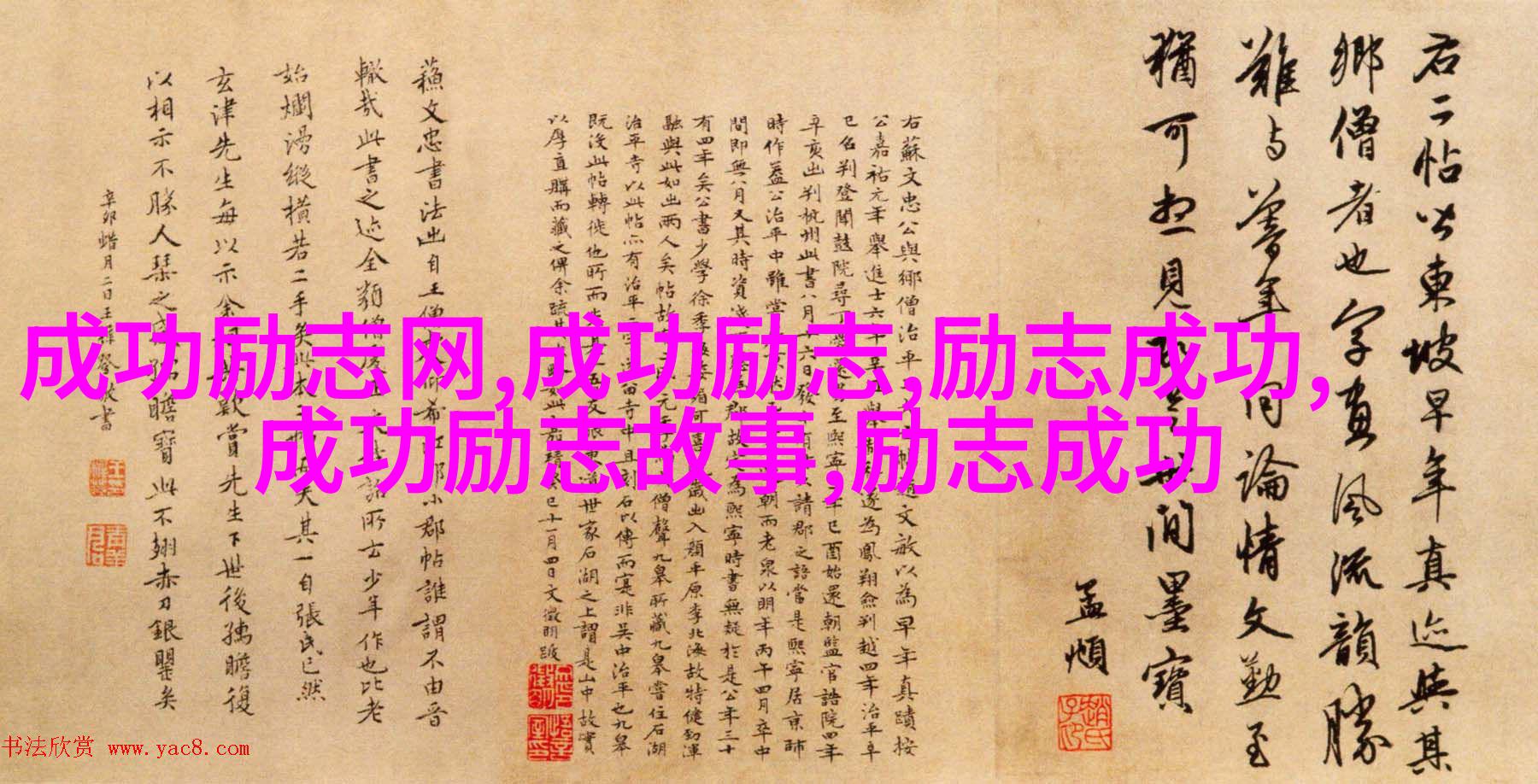
多年以后,当 吉姆 的母亲去世时,是 雷守护她的灵柩;不到一年时间又是父亲离世依然站在我们身边,还送出了曾经一起使用过的地盘。这段友情至今仍坚不可摧,即便两人再也不纵情豪饮,每次聚首第一轮依然由 雷请客,并且始终从那第一瓶 酒中取出的,是永远的acidic fruit ju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