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如同一杯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人说我一直很顺利,我只能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长达5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是事业上的挑战还是心态上的波折,都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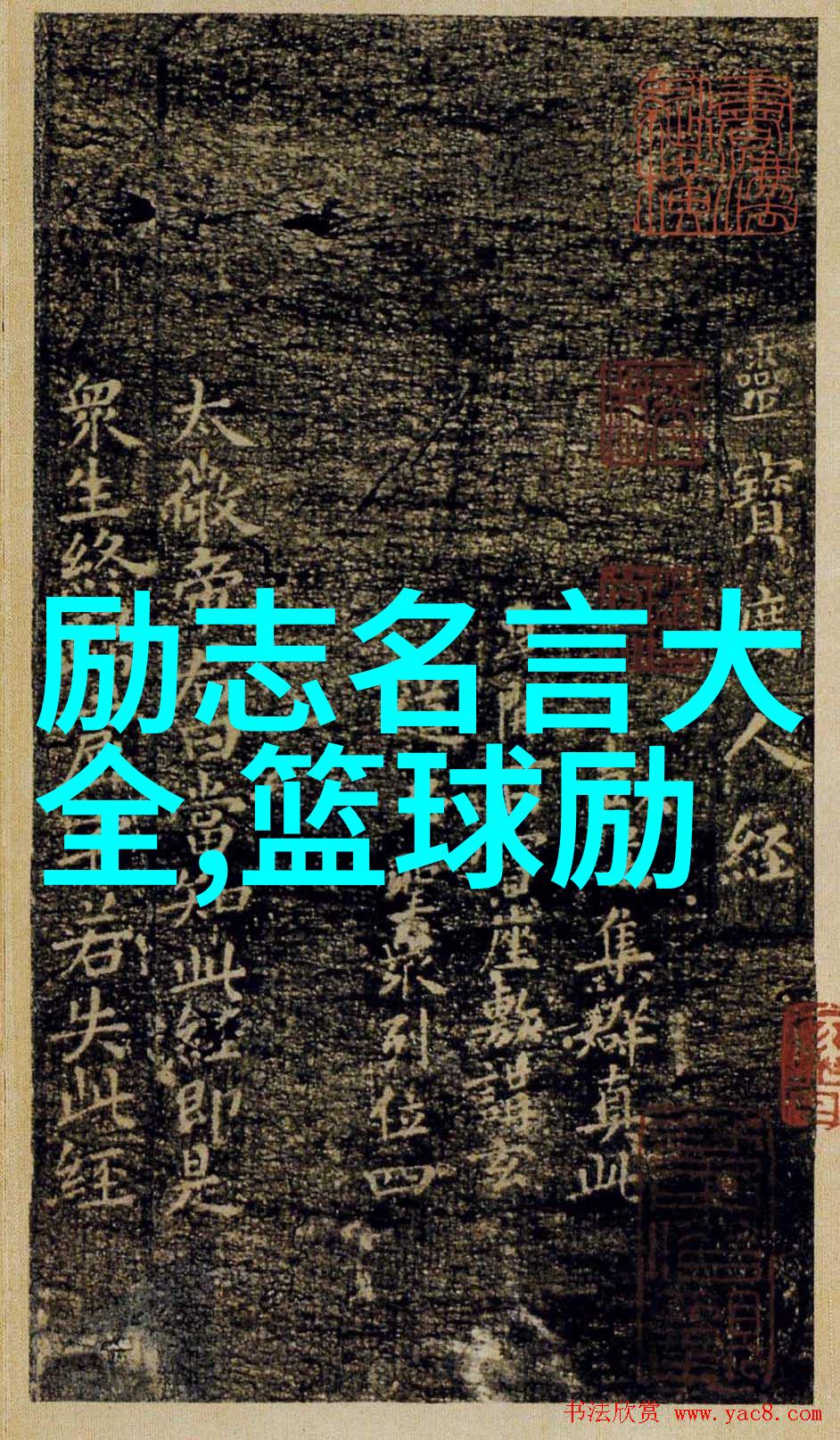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那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但我觉得这不符合我的职业定位。我对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文化行业,与IT、商业、金融和工业完全不同。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回来的。当结婚时,我就跟吴征说清楚了:“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通过采访王光美,她不仅成为节目的一位重要人物,更是我人生中极大震撼的人物。她的事迹激发了我记录历史与时代关系的热情,从而确定了一点——通过采访人物记录历史,是我的节目目的之一。这份热情源远流长,从中学就开始萌芽。在大学期间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时,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如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等伟人的影响力也深刻地铭刻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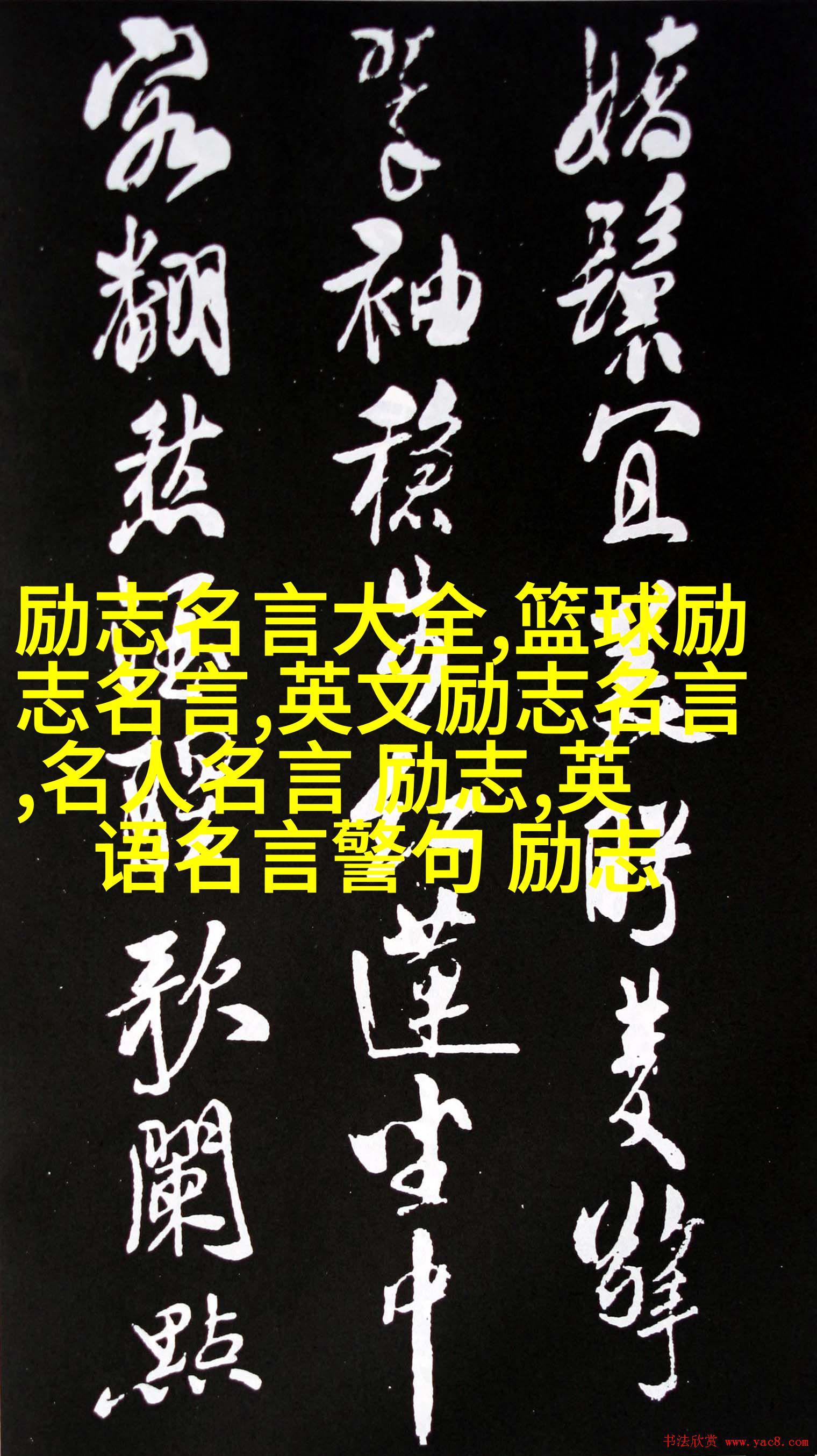
作为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当时中国传媒系统还未形成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不断探索创新的路径。在阳光卫视期间,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也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不断尝试与调整,最终发现市场规律背离我们的初衷,我们可能过于急切,不够审慎。
然而,在那五年的奋斗中,我哭过很多次,因为我们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与商业风险交织,让整个经营团队及投资方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而最终的是吴征的话语给予了指引,他鼓励并且提醒:

"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现在必须要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和现有平台的一个最好的负责任的方式。”
他的话像一把刀割开迷雾,让我明白一切,只有勇敢面对才能找到出口。所以,在2003年的夏天,当决定出售阳光卫视后,一种释然感油然而生,而不是愧疚或失败。

尽管如此,每一次成功后的赞誉,以及那些支持者的鼓励,都让这一切变得值得。一场风雨之后,有些东西被磨练得更加坚硬,而有些则被抛入过去。而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学会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理解世界,并以此为基石,再次踏上前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