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那个曾经我从未踏足却深深迷恋的地方,它的故事,是一段关于时间、空间与记忆的交织。

1937年,一座名叫宁静饭店的地标性建筑站在黄浦江边,仿佛一个高跟鞋下的女郎,她现在已经老去。每当人们提起她,他们闭上眼睛,就像回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一样。那楼上的长廊安静温暖,被青铜壁灯照亮,有时门扇会打开,从里面走出三四十年代的人们,如恩雅和岑寂。
他们穿着前面有一根抹筋的玻璃丝绸,男人抽烟如同时尚的埃及香烟。在吴宇森电影《宁静饭店》中,他们讲述了一个男人的故事,而那个时代没有那个故事,但那个时代总是例外。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共鸣是我所喜爱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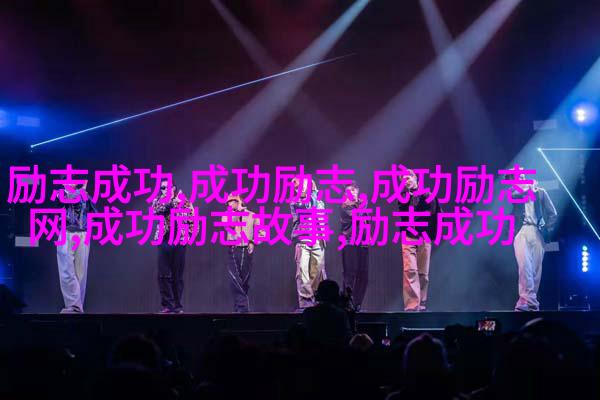
岑寂在咖啡屋里跳针,一圈一圈转着,有时候偶尔碾到唱片上细尘之上,这声音只有在好久以后被“小燕子”、“穿花衣”的童声大合唱相伴时才留下——“小燕子(swallow),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简朴而轻巧,每个过程都有许多省略掉的事物。
恩雅说:“我现在走在东山的小巷里常常会反思自己的一生,而也许我的一生就象这一条小巷,暗淡的路灯,暗淡的光,人走在里面,就像剪纸贴在上面。却很自然。”

那条小巷有个新鲜利益,不管它建得多新多晚,都很快变得古老,就像我眉间鱼尾纹。但是我依然喜欢一圈一圈地走着,就像那些老旧留声机上的唱片,上面隐藏着忘了通知你的声音,那些留声机也是上海出的,用起来粗笨耐用。
到了小巷终点,有张竹椅。一位老人坐在竹椅上,他眼神半睁半闭地与小巷私语,小巷似乎听见,又似乎不再听见,也许。

岑寂看着咖啡馆外面的世界,那时一个小姐走了过来。她推荐了一杯盐汽水,并提到荠菜肉丝加年糕也不错,还有五香茶叶蛋加豆腐干。不过他明天带齐了上海小开三件宝:怀表、皮带、皮夹子,所以小姐说话很多,是因为他的身份让她想说更多的话。而他将带两张去香港船票,现在什么都不值钱,只除了黄金和美圆。他自从留学返来一直在英资银行工作,也就是那时候他熟悉恩雅的事迹。
某个平安夜,在宁静饭店顶层舞厅内华灯缀满今宵不夜。当年的租界时代舞厅是西洋人的娱乐场所;敌伪时代则因人口畸形增加而繁荣,但失去了真正高尚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习惯于回忆习惯于回到已往,那么你永远活在已往并且活下去,便是一件好事儿。而她沿淮海中路行走,他目光追随她的身影,她遮住了他的世界,从那个平安夜过后开始。她知道幸福生活便藏于此处,却又容易遗忘,当欧洲人寄信给故乡描述我们熟视无睹历史,比如1914年洋泾滩填土成爱得加路,我们只知道延安中路比如第一家跑马场正式营业,比如剧作家写下上海……他们只是普通市民:一个英派青年、一名罗敷女职员,以及那些未曾言说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过去与现在交汇点的小城市,一段关于时间与记忆编织的小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