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花吃。

英语里有个不怎么美好的形容词叫“weird”,当某人被评价“He/Sheisweird”时,他多半是不受欢迎的,要么孤僻阴郁不合群,要么怪异另类难理解,这样的人,在生活里大多被边缘化。在电影里却常常因为人性挖掘的需要而成为主角,比如《天使爱美丽》里的艾米莉。
艾米莉就是一个weird的不得了的小孩,童年的时候,父亲给她做健康检查,发现她心跳过快,便断定她患上了心脏病,从此艾米莉与学校绝缘,只在家里由父母教授。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她一个人忍受冷淡的父亲和躁郁的母亲,在倍感孤独的同时,渐渐生发出自己的天地,在她的世界里,一切都妙不可言。

说她是怪胎也是可以的。可怪异如她,也在偌大的巴黎找到了爱人,那个人懂她所有奇思怪想的躲藏游戏,能发现她所有含蓄繁琜的心理活动指引,也洞悉她久积而成的心生懦弱。当影片最后,艾米莉把头埋在心爱男孩间,一起骑着摩托车飞驰而去的时候,我觉得很震动。她遇到了他,他找到了她。
第一次看《天使爱美丽》的时候,我刚刚带着一堆幻想步入大学,当时只觉得风格奇诡色调明艳,一下子被法国人浪漫到不行的一种叙事方式轻易虏获,不明就里的激动得不行。那之后到现在,又刷过好多次,最最近一次是在上周,时光流转物换星移,再看它时的心情早与第一次大不同。

我愿意相信,我想要去相信,无论你是何种样子,都有人与你相契。毕竟,“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我的生活平庸,但身边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怪人才”,TT算得上一个,她已经结婚。我常对TA说,有关于你的事情中,有一件我大概会永远记得,每每想起来都觉得莫名感动。她在生日的时候和TA彼时还是男朋友通电话,说“我想给你唱一首《我的祖国》,没错,就是那首‘一条大河波浪宽’……”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心胸多宽广”。
如果说我期待某种爱情状态,大概和这有些类似。我早已不是满脑子粉红泡泡的小姑娘,但也曾幻想过自己会与一个怎样的人相爱,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人拿我的年纪、我的同龄、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做着加减乘除运算企图给我一个最优解时候,我仍然是不甘。我负气地想,我宁愿蹉跎岁月,让你们口中的反面教材也不愿意成为婚恋市场上的商品,在物品价值和人的尊严之间,我要选择后者。我要选择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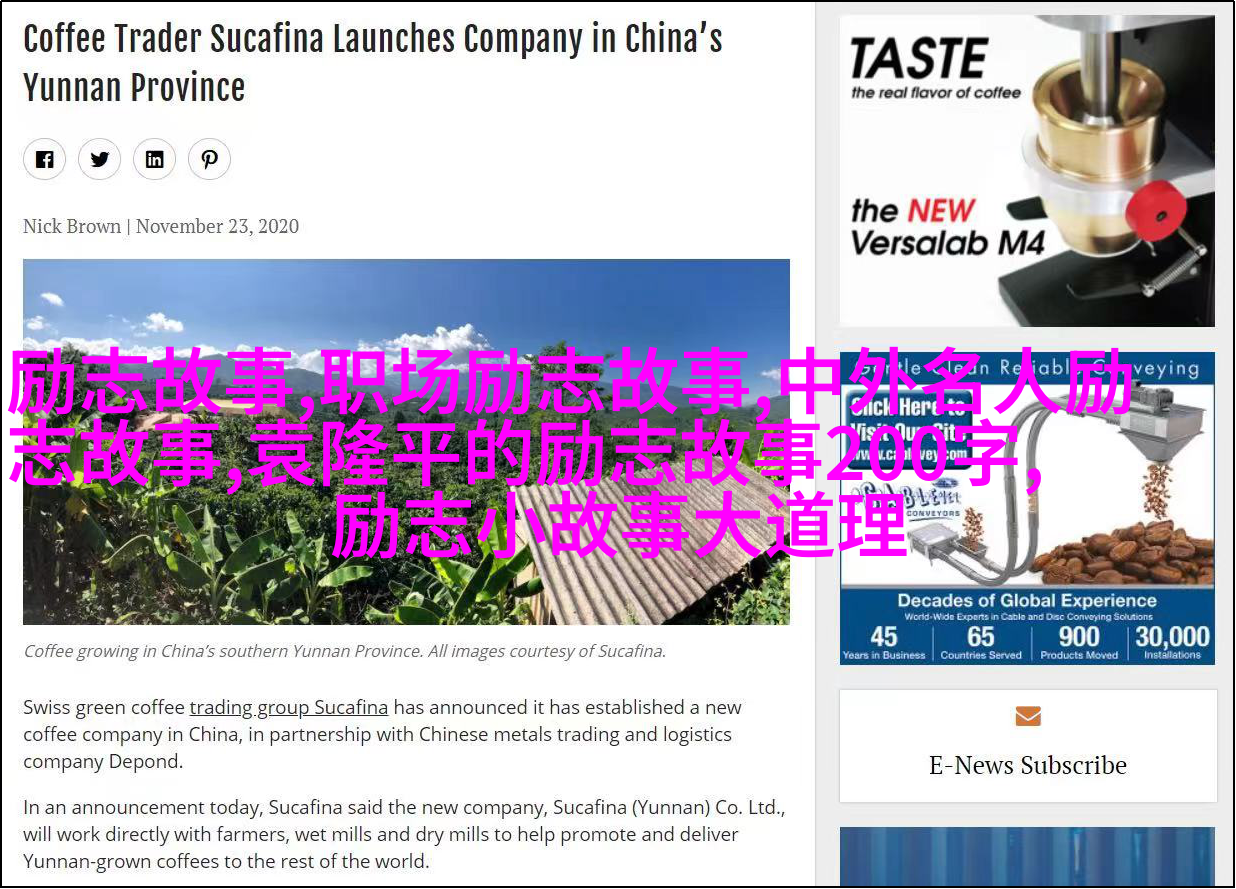
当我这样跟别人说的时候,被很多嗤之以鼻回应,他们觉得我还在空中,还未褪尽少女幻想,对这个时代爱情与婚姻本质完全不知他们对我露出那种过去无往不利笑容。一副既惋惜又好笑样子。我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真诚表达希望找到自然相遇的情侣、期待精神相契的情侣成了一件如此羞赧的事情呢?
可笑的是,即便社会巨潮之中的我们自身也察觉哪怕是这点勇气和执念,都正在渐渐弱化消失,我们已经都不敢再从容表达这样的幼稚观念,对于我们的看法也日趋现实。但是我从未说服过自己,我仍然挣扎困惑每到这种时候,就会看《天使爱美丽》,当然跟艾米莉并不相像,但总感觉她的故事是一股推力,在我们之间欲拒还迎地周旋时,是帮助我们推开了它。拒绝的时候,我弱弱地说:“你或许还在来的路上。” 我仍然想要候候您。你前进路上的三只虎,请不要忘记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