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我所经历的艰辛和失败

我的生活如同一杯茶,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只能无奈地微笑。我无法向每个人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的五年时间里,我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是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1996年,我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成为他们的记者,但我觉得这不符合我的职业定位。我对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文化行业,与IT、商业、金融和工业截然不同。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回国。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四个字来形容我。这几个字在他身上倒是恰当,他似乎放弃了什么,而我并不需要放弃任何事情。

1997年,我连续了一整年没有工作,只做生育和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凯卫视开始制作《杨澜工作室》。
采访王光美是我节目中最震撼的人物。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也让我深刻认识到作为记录人与时代关系的一种方式——通过采访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对历史的热爱始于中学。当时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都是激励我的榜样。在高考前期,有一次特别想要报读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职业理想。

我有着文化理想,为中国缺少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而感到焦虑。这就促使我去做阳光卫视,从2000年开始制作以纪录片为主体的节目。
入行企业有点像迷失方向。我是个内容出身的人,不料意外地陷入渠道运作中。出发点是为了内容,然后为了这个内容搭配相匹配的运作机制。这有点像养牛奶,就因为市场上没有卖这杯牛奶,所以必须自己养牛。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做类似的事情,这样就形成了一股产业力量。

当然,那些日子充满挑战。在学国际经济但实际操作完全不同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选择。一切似乎遥不可及,因为美国传媒系统已经完善,只需专注最擅长的事业。而我们则在开放过程中寻找合适路径,以市场规律为导向发展,这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风貌,或许三十年后,我们这些选择将不会再那么复杂。
吴征最初鼓励我转型,但那转型极其困难,一次又一次跌倒,就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那份冲动远超商业知识水平。起初创立阳光卫视未能做好商业判断准备,我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电视制作中心,在香港耗资数千万,每年的原创节目数量达到几百小时,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决定性错误。此外,由于收入模型尚未稳定或实践得到肯定的公司,上市后的财务报表要求引发矛盾,对整个经营团队也给予巨大压力,并且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让人哭泣多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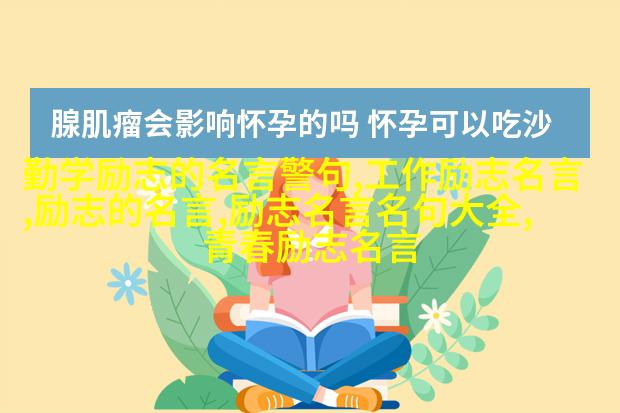
那几年的挫败感让人难以平静,即使吴征理解并支持他的努力,他也提醒要学会放弃。他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必须变成现实主义者,要考虑这个问题。”他的话让我深受触动,最终决定出售阳光卫视,结束这一切痛苦劳累之旅。
虽然阳光卫视遭遇商业上的失败,但它对于推动国家级别纪录片频道开辟具有重要意义,是第一个尝试结合文化与商业模式的人们探索之路,如今人们已经清楚知道哪条路可行哪条不可行,那段经历至今仍被记得并被肯定,让她感到温暖满足。
最后,她选择继续工作,用不断努力来平复内心的情绪,她继续拍摄《杨澜访谈录》,接着又开始拍摄《天下女人》等项目,并逐渐扩展到了其他业务领域。她认为这样的调整也是战略转型的一个良机,使得公司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中的媒体环境。
目前,她拥有三个主要业务板块,其中之一基于《杨澜访谈录》的精英阶层社区影响力;另一个基于《天下女人》的都市白领女性社群影响力;以及第三个涉及多媒体经营战略转型 hers is a story of struggle and failure, but also one of resilience and grow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