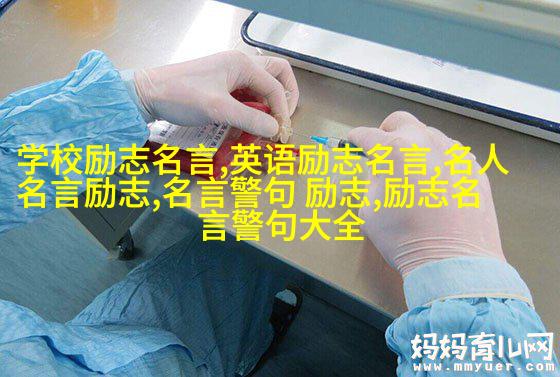我的生活如同一杯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人说我一直很顺利,我只能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长达5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是职业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与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与IT、商业、金融和工业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通过做节目,就特别感受到记录人和时代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决定以采访人物方式来记录历史。这一点其实早已埋下种子,当初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时,对历史便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高考前夕,即曾梦想报读历史系。但这些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最终促成了我的职业理想。
但愿意成为一个文化平台,在中国传媒市场这个特殊环境中,是一种挑战。当时市场上的现实让我不得不面对转型困难,一开始就遭遇重创,那就是阳光卫视。那是我为实现文化理想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对于商业运作知识水平不足的一个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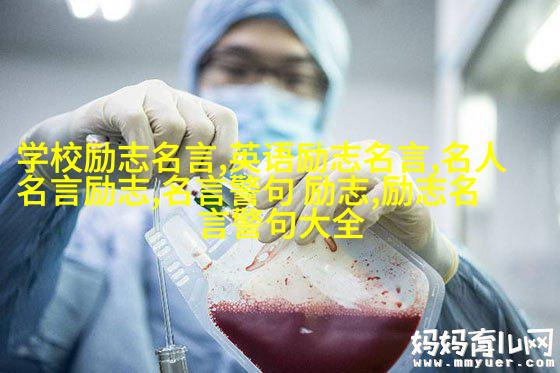
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学习,从最初只是一家小众纪录片制作中心慢慢发展至拥有大量原创节目,每年的数百小时内容输出,其实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后来意识到了幼稚之举,当时热情洋溢地让吴征参观新建的大型制作中心,他吓了一大跳,当即警告:“你们拉这么大的摊子,是要出事。”那五年的时间里,我真的很累,并且事倍功半,现在看来这一切也许只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当你的商业模型不对时,你越做越累,并且往往事倍功半。
那些日子里,有过许多泪水流落,而最终能量来自于不断工作。在此之后,《杨澜访谈录》继续深耕细作,同时又推出了《天下女人》,并逐步建立起多元化业务结构,如天女网、澜珠宝等。此次失败更成为一次战略转型机遇,让公司从单一平台变为内容提供商。而今,我们已经拥抱多元经营,为未来奠定坚实基础。在未来的岁月里,或许能看到更多成功篇章,而这些挫折或许也是通向辉煌的一条必经之路。